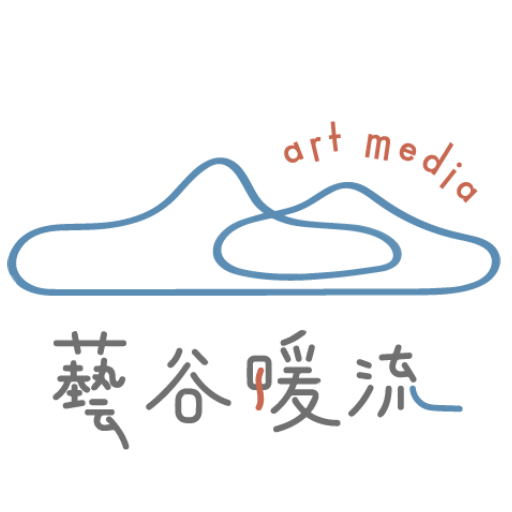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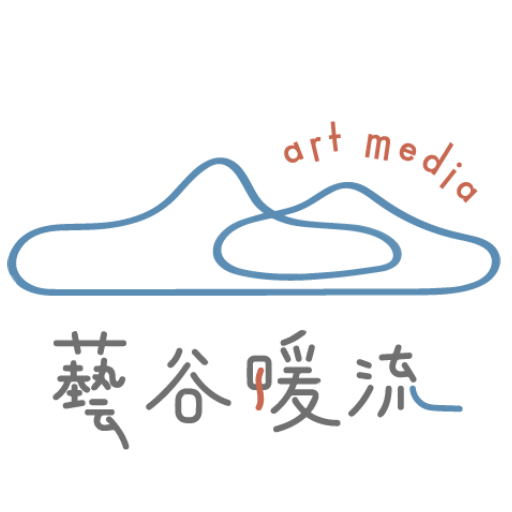

尼可・艾森曼(Nicole Eisenman)的個展「墮落天使」(Fallen Angels),就像標題中落入凡間的天使一般, 是她近年來最為入世、最貼近生活的一次呈現。展覽涵蓋十一幅近期繪畫與三件雕塑,主要聚焦於三個中產生活的典型場所:家庭、工作與海灘。展出的畫作幾乎全為架上尺寸,而其中的兩件雕塑(取材自艾森曼工作室裡的桌子與椅子)即使脫離了原本的使用場景,仍帶給人一種不經意的現成品(readymade)之感。這些作品尺幅的收斂與靜謐的基調,與藝術家以往擁擠群像和充滿社會諷喻的風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,但它們同樣不容小覷。在這裡,人物徘徊、猶疑、自我反覆,時間彷彿在熟悉的空間中凝滯。畫面追求的並非製造視覺奇觀, 而在於凝視,在於持續直面近在眼前之物的考驗。前兩個場所(家庭和工作)已彼此坍塌、融為一體,第三個(海灘)也未提供任何逃離的出路。
這些作品中有一件與眾不同。這幅與展覽同名的繪畫作品,就像是王家衛1995年那部新黑色電影《墮落天使》的一張海報。乍看之下,它置於展覽中那些描繪家庭與工作生活的靜謐畫面之間,似乎顯得格格不入;但一旦你想起這部影片全部是在夜間拍攝,你便會意識到它正是理解整個展覽的關鍵。幾乎在每幅畫中,只要看向窗外或仰望天空,我們就能立刻發覺:對艾森曼來說,外部世界是一片黑暗,而且正在變得越來越暗。
在《一個好的起點》(A Good Place to Start,2025)中,從紅色窗簾掩映的窗戶中瞥見的天空近乎帶有一種暴烈之感,而在窗下杯中的咖啡則令人想起荷馬筆下「酒色般幽暗的海」(wine-dark sea)。這種去時間化的效果為原本克制的構圖賦予了一種史詩般的陌生感。《倫納德街》(Leonard Street,2025)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海天意象,但整體場景更加基於帶有黑色電影氣息的都市符號。一個男人龐然矗立於街區之上,用火柴點燃香菸;一隻黑貓在他腳邊潛行。人行道看起來濕滑、泛著虹光,甚至透露出幾分危險:人們是有可能太過迷戀油彩顏料的。

痛苦亦在作品中不時閃現。在《趕工中的自畫像》(Self-Portrait With Deadline,2025)中,藝術家坐在一張小桌前,桌上擺著一瓶薊花,正試圖完成一幅靜物畫。在她身後,陰影中的牆面染上了花朵般的藍紫色調。然而,她筆下的畫紙卻隱約泛紅,默示著好像哪裡不對勁:那沾在藝術家指關節上的,究竟是胭脂色顏料,還是血跡?
表達思想的困難是艾森曼反覆探討的主題之一,而她的創作恰恰以一種看似輕鬆自如的方式將此呈現。《處理中》(Processing,2025)厚重堆疊的筆觸下潛藏著十幾幅失敗的畫作,而作品的標題顯然也是一語雙關。在最終完成的畫面裡,兩個手指木偶似的簡單人物在一片明亮的淺色背景上交談。象徵著私密話語的,是一連串空白的對話氣泡,它們在兩人頭部之間及周圍瀰漫開來。奇怪的是,這兩個腦袋似乎在節節後退,空氣也彷彿變得愈發沉重。雷內・里卡德(Rene Ricard)曾試圖向一位朋友解釋這種人物與背景關係的巧妙反轉,但對方未能理解,說那「不過是藝術家塗抹顏料的方式」。里卡德對此頗為震驚:對他而言,同樣也是對艾森曼而言,顏料塗抹的方式本身已然意味著繪畫意義的全部。

層層疊疊的中介(mediation)與反覆修改所留下的物理痕跡,貫穿了整個展覽。若說畫中的物件似乎取材於現實生活,那麼人物形象更像是源自記憶。《伊迪》(Edie,2025)表面上是藝術家寵物的肖像,但畫中貓的頭部呈現出一種近乎埃及式的古老氣質,彷彿並非實物的寫生,而是描摹了青銅雕塑《瘋貓》(Mad Cat)。就連孩童的形象都讓人感到陌生。《霍普街道:費雷迪與喬治》(Hope Street with Freddy and George,2016–2023)讓人得以一窺艾森曼在創作中偶爾顯現的、近乎執念的反覆改動過程。她在長達七年的時間裡斷斷續續地創作這幅作品,甚至在2022年展出一次後再度將畫作帶回工作室進行修改。這樣的時間跨度讓畫作中的滿足感顯得來之不易,卻又讓人隱隱感到不安。檯燈亮起,氛圍祥和,但窗外卻露出一片泛著藍光、愈加昏暗的天空。

不浪費的積累,是艾森曼在工作室實踐中的核心原則,因此便有了《香蕉吊燈》(Banandelier,2022)。這是一件不發光的吊燈裝置,風乾的香蕉皮取代了傳統的水晶吊飾。艾森曼並不指望《香蕉吊燈》可以售出,但如果真的成交,買家將會獲得一段45秒的教學影片《如何剝香蕉》(How to Peel a Banana),以便在家中自行重製拼裝作品。這並非玩笑。香蕉是艾森曼最愛吃的食物之一,也是她最鍾愛的象徵——一種既像清晨般可靠,又如人類存在般易於腐爛的水果。在這件作品中,她援引的並不是安迪・沃荷(Andy Warhol)或毛里齊奧・卡特蘭(Maurizio Cattelan),而是同為性少數藝術家的佐伊・倫納德(Zoe Leonard)。倫納德的雕塑《奇怪的水果》(Strange Fruit,1992–1997)致敬大衛・沃納羅維茲(David Wojnarowicz),同樣用到了被掏空後再以紅線重新縫合的香蕉皮。畢竟,香蕉本就是滑稽劇般的水果,在腐朽中仍然保持樂觀。
海灘題材的繪畫《我的噩夢》(My Nightmare)、《七月五日》(Fifth of July)和《海嘯》(Tidal Wave)均創作於2025年,它們印證了室內場景中早已暗示的結論:我們無處可逃。《我的噩夢》中,一名救生員俯視著一群類人的形體,如殭屍般走進一浪又一浪的糞污海浪之中。《七月五日》中,擬人化的臃腫帝國身著藍色浴袍和紅色條紋短褲,神情沮喪地牽著一隻小狗,從一堆不知是戰利品還是廢棄物的東西旁走過。(熟悉艾森曼創作脈絡的觀眾,會從這堆彷彿從垃圾船上被沖刷到岸邊的物體裡,辨認出她在其他繪畫或雕塑作品中用過的元素。)在這些畫作中,顏料在同一幅畫面裡發揮著不同的功能:在海浪與沙灘處厚重地堆砌,又在人物形象上趨於平面。顏料以自身的具象性(或者更準確地說,以其物質性和這種物質性帶來的種種阻力),對抗著作為符號的「人物形象」本身。在《我的噩夢》和《七月五日》中,地平線被推至畫面頂端,整個畫面幾乎被砂礫覆蓋,或被沙色的水灌滿。這帶來了一種沙漏般的效果,沙漏翻轉,從六十開始倒數,時間不多了。最後, 艾森曼在《海嘯》中刻畫了屬於她的「歷史的天使」(angel of history)。她背向未來而坐,目光在沉思中凝定,試圖放鬆,忘記過去。艾森曼說,逃避主義是一個好笑的悖論。一片滔天巨浪即將拍岸而至。
資料來源及圖片來源:豪瑟沃斯畫廊